民国诡案录张佳竹完结了吗,民国诡案录张佳竹txt下载,民国诡案录第四部,智能火独家提供《民国诡案录》小说章节目录及全文完整版(文修书),民国诡案录小说主角文修书全章节免费阅读,《民国诡案录》主角小说讲述的是:二十年前,没人知道文修书的来历,只知道他突然就出现在了树上,二十年后,长大成人的怪异孩子开始调查当年的真相。
免费阅读
我大吃一惊,还以为他跟我说着玩呢,可是看他的眼神,一点玩笑的意思都没有,还是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看了他半晌,才道:“你疯了吧,找爹找疯了,认个女人当爹,你倒是想,可也得人家愿意啊。”
阮郎急了,从床上蹦了起来,坐在床沿张牙舞爪地跟我理论,就跟我不让他认祖归宗似的,说:“我看到了,真的是它,真的是它!”
我被他说糊涂了,打断他的话,道:“你先别急,真的是谁,你看到了什么?从头说起啊。”
阮郎呆了呆,才道:“那把剪子,上面刻着我的名字,一边是阮,一边是郎,合在一起就藏到了刀锋里看不见,是我娘为我爹打造的,让他换青丝时用的,绝不可能有同样的一把剪子。它就张着放在那桌上,我看见了。”
我顿时哭笑不得,道:“就凭一把剪子,你就敢认一个女人当爹,不对,你是怎么能看见那把剪子的,你偷进人家里了?”
阮郎摇头,道:“昨天有个人叫我今天去收青丝,我正打算去,从一户宅子的后门走过去的时候,那门忽然打开了,那女人走了出来,跟我说她要换青丝。我一见是她,还吃了一惊,她昨天骂我,今天却又要跟我换青丝,不过有生意上门,我总不能不做,就把车子停下,站在后院里就要给她落剪,她却又说要照着镜子自己剪,让我跟她进了房间,就在镜子旁的桌子上,我看到了那把剪子,左边刻着阮,右边刻着郎,绝不会有错的。”
我问他:“后来呢?你没问她为什么有你爹的剪子?”
阮郎道:“后来,她看着镜子忽然哭了,我也不敢再去问她,她也说青丝不剪了,就把我赶了出来。”
被他这么一说,我顿时也大感蹊跷,嘴里还是道:“这也只能说明罗夫人和你爹和有什么关联,你怎么能说她就是你爹?”
阮郎摇摇头,道:“我觉得她就是我爹。”
我摆出一副愿闻其详的样子来,阮郎看着我,道:“她跟我爹一模一样,我不是说她长得像,而是举手投足间和我娘说的一模一样,你发现没有,她走的是外八字?”
我干笑一声:“我又不找爹,去注意她干嘛?”
阮郎白了我一眼,道:“她没走两步就会下意识地垫垫脚,那是货郎推着车子走山路时的习惯,垫垫脚才能使得上劲,最重要的是,”他说着忽然顿了顿,想了想,才十分郑重地道:“在她的肩头,有一个牙印,她撩起青丝的时候,我看见了,一个牙印在左肩那里,那是在成亲的第一天,我娘被我爹吓坏了,扑在他肩头咬的,咬得太狠,印到肉里去了,怎么也退不掉了。”
“你说,”他盯着我看,“这世上有这么凑巧的事吗,一个人有我爹的剪子,又和我爹在相同的地方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牙印?”
我也觉得这事太过巧合,不过我还是问他:“假设你说的都是真的,可是,你爹怎么变成女人了?我见过那罗夫人,绝不可能是男扮女装的,我知道有的男人是会变成女人的,可那是要从小当女的来养的,就算这样,只要仔细看还是能看出不一样来,绝不可能像你爹那样,成亲之后还能忽然变成女人,而且,她还有个儿子,据我所知,就算男人变成了女人,也绝不可能生孩子的。”
阮郎被我说得半晌无语,良久才道:“这些我都知道,也搞不明白,可我就是觉得她像我爹,就算没有那把剪子,没有那个牙印,我还是觉得她像我爹,先生,你是读书识字的人,总知道‘父子连心’这句话吧,我们只相处了一会儿,我就觉得对她有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。”
我质疑道:“有没有这么玄乎啊?”
阮郎见我不信,又急了,道:“指天发誓!先生,我说的都是真的。”
我道:“好了好了,这事你可别声张,等明天我们打听打听,那罗夫人是什么来头,如果她不是本地人,而是忽然出现在这罗联镇上的,那她就大有可疑了,我们再慢慢打探。”
阮郎闷闷地应了我一声,又躺回床上,然后在床头摸了摸,扔给我一个东西,说:“是你的书吧,怎么扔我床上了,我翻了翻,认识六个字,先生,这些字你都认识么?写了些什么?”
我接过那书,那是我早上看的时候顺手扔到他床上的,嘴里道:“巡城马代写家书,全靠识字才端上一个饭碗,能不认识这些字么?至于这书么,是送信途中无聊解闷,打发时间用的。”
阮郎“哦”了一声,明显没有兴致追着问,我也不去理他,挑亮了油灯,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,直到眼睛酸涩,才将灯吹灭,和衣睡了,这时阮郎早已鼾声大作了。
第二天我早醒,醒来的时候阮郎还在,我们一起去前面吃早餐,我向店主人打听:“主人家,这罗联镇上一半的田地在罗夫人手里,那她肯定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吧?什么时候嫁到罗联镇的,又是什么地方的人呐?”
店主人闲着没事,坐下和我们闲聊:“哦,这罗夫人,倒不是山外嫁进来的,她就是这镇上的人,我从小看着长大的,至于大户人家出身嘛,这罗联镇上除了罗家,哪还有什么大户人家,她也就出身小门小户,充其量算小家碧玉,充不得大家闺秀。”
我眼角斜了一下阮郎,示意他,罗夫人既然是罗联镇上土生土长的,肯定不能是他爹,嘴里对店主人道:“罗夫人操持这么一份家业,还得顾着孩子,哦,她应该是在孩子长大后接手这份家业的吧,不然哪里顾得过来。”
店主人摇头道:“那孩子还没生下来,罗家老夫人和她丈夫就相继去世了,据说是患痨了,绝症呐,那孩子是遗腹子,有娘生没爹教,所以才一个劲败家。”
我“哦”了一声,心想,又一个遗腹子,这下连罗夫人生孩子的事也坐实了,她就更不可能是阮郎他爹了,嘴里问店主人道:“那孩子什么时候生的?”
店主人说了个时间,阮郎喃喃道:“比我小,是在我之后生的。”店主人有点耳背,问他:“你说什么?”
阮郎道:“没什么,请教主人家,你还记得么,十几年前,有没有一个也姓阮的货郎打这里过去?”
店主人邹着眉,想了想,道:“十几年前的事啊,你容我想想,要是有客人到罗联镇来,都是住我这里的,除了我这没地方住,罗联镇藏在山里,平时也少人来,这十几年嘛,总共到过的货郎也没几个,有一个常来的货郎姓蒋,还有的都是打这里过。”
他摇摇头,断然道:“没有姓阮的货郎从这里过,倒是有一个巡城马姓阮,住过我这,但也只来过一次,后来再也没来。”
说着,惊疑地看着阮郎,道:“这位小先生也是姓阮,也是货郎,找的又是十几年前的阮货郎,莫不是?”
阮郎苦笑了一下,道:“我爹十几年前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去,我这一趟出来,顺便打听一下他。”
店主人恍然大悟,连连摇头,道:“没从这里过去,住我这的货郎我都记得,唉,出外讨生活的,回不去的不少啊,世道不太平。”
我们又闲谈了一会儿,阮郎大失所望,同时更觉蹊跷,他爹从没从这经过,那罗夫人却怎么会有他的的剪子?我们都想不明白,他也就出去叫卖了,我回到屋里,又看了几页书后,有人来请我去写家书,我就将书扔在了床上,出去了。
出乎我意料的是,这一天竟有如此多的人要写家书,我从早上出门,中午回来吃了午饭,还没来得及回后屋,就又被人叫走了,在外面又是一整个下午。写完最后一封家书。我才伸展了一下,笑着对那户人家说:“不曾想在罗联镇竟有如此多的人光顾我的生意,托你们的福,希望今年是个好年景。”
那人笑起来眼睛只剩下一条缝,说道:“要说这家书,写也成,不写也成,山里人家的,剩两个闲钱不容易,出去的人时候到了,自然也就回来了,又不是走了十年八年的,写什么家书呐?只是吴主家心善,说巡城马来一趟不容易,让我们要写家书的都尽管去麻烦先生,钱由他来出。”
我心想怪不得今天这么多人要写家书,原来是不用自己出钱,这位吴主家倒是心地好,愿意出这份钱,也让我跟着沾光,倒是要好好感谢他才是,就问了他是哪位吴主家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他说的这位吴主家,居然就是我之前在店里见过两次的,总是和罗夫人的儿子一起出现的那位。店主人说他净骗小孩,哄着罗夫人的儿子赌田地,赢了他不少田契,言语间对他颇为不屑,不曾想倒也有如此善举,大家对他评价也颇高。
从最后一户写家书的人家里出来,回到店里的时候,天色已经大黑,我请店主人为我煮一碗面,这时阮郎从后面走出来,叫道:“请主人家多煮一碗,我也没吃。”
他在我对面坐下,兴致还不错,我猜他今天卖得也不错,才会这么喜形于色,就开口问了他,他却道:“山里小镇,叫卖了两天,今天哪里还能做成多少生意,我出去,只是想看看能不能收些青丝罢了。”
我问他:“那可收了些回来?”
他应道:“总共就收了一份。”虽然总共就收了一份,但看他神色却很高兴,我想起他第一天晚上对我说起过,镇尾有一个姑娘让他第二天去收青丝,并且说那姑娘对他好像有那个意思。他昨天被罗夫人的事干扰了,并没有去收,想来今天就去收了。我告诫过他,我们走村串户的人,千万不能去招惹什么不能招惹的人,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,我却也不好再去说他。
阮郎兴致勃勃,一个劲地道:“那青丝特别好,油黑发亮,发着一股黑光,等下我进去拿给你看。”
店主人把两碗面端了过来,我们就着油灯吃完后就回到了后屋,阮郎果然拿出包裹要给我看那青丝。他把包裹解开,将盘得齐整有致的青丝掏了出来,朝我夸耀道:“先生,你看呐,这青丝,卖到梨园里,铁定能拿一个好价钱,你猜她要了我多少钱?那姑娘心地真好,说我们货郎不容易,几乎白送给我的!”
我瞧他说得唾沫横飞,故意泼他冷水,道:“这青丝是挺好的,不过呐,下面小心别连着颗脑袋才好。”
阮郎笑道:“先生从我这听了故事,倒用来吓唬我,好吧,让我来看看,这姑娘送我头发,是不是连脑袋都送给了我。这里面真有个圆鼓鼓的东西,我不记得我装了什么在里面了。”
他一边说着,一边将青丝往外掏,手上一用力,顿时就将所有青丝都拽了出来,青丝下面还连着一个圆圆的东西,他嘴里还在说:“咦,这是什么?”我却早已看清了那东西,顿时就惊恐地一声大叫,吓得几乎昏死了过去。
那缠绕不清的青丝下面圆鼓鼓的,正是如假包换的一颗姑娘脑袋。
阮郎被我叫得一哆嗦,这时候也看清楚了手里拎的是什么,也是歇斯底里地一声尖叫,把手里的东西甩了出去,然后直挺挺地往后一仰,栽倒在了床上,居然吓得昏死了过去。
我们两个相继尖叫,自然惊动了店主人,他端着油灯摸了进来,嘴里叫道:“两位先生,出了什么事了,如此惊慌大叫?”
进得门来,一眼看见我们两人,一个窝在床上一动不动,另一个面如死灰,面容呆滞,地上有一个圆滚滚的东西。他年纪有些大了,眼睛不怎么好使,一时不知道地上的是什么东西,还蹲了下来去看那东西。
我眼睁睁看着他凑近了那脑袋,还用手去提那头发,有心要提醒他,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话来,只得看着他提起那脑袋,放在眼前仔细地瞧了瞧,这才一声闷哼,跌坐在地上,然后连滚带爬,一边踉踉跄跄往外跑,一边大喊:“杀人了!杀人了!杀人了!”真难为他一把年纪跑得这么快,还能叫得这么大声。
店主人就是保甲,本身就负有维护治安调解邻里纠纷的职责,在他店里发现了姑娘脑袋,自然马上报告了镇公所,镇长很快就带着乡勇赶到,将阮郎一桶水泼醒,然后和我一起带到了镇公所。
事情说起来倒是容易,我在镇公所里,三言两语把事情交代了,阮郎去掏青丝,却掏出连在下面的的一个脑袋,阮郎和我说的一般无二,并没有狡辩那脑袋不是他从自己的包裹里掏出来的。镇公所的人见事实清晰,倒没有为难我,很快就将我放了出来。
至于阮郎,镇公所的人认定他以换青丝为由,恶意将一个姑娘杀死,并剪下脑袋藏在包袱内,带回住处,向人炫耀,他那包内藏着的剪子还沾着血迹,似乎就是用剪子将脑袋剪断的,罪证确凿,关押在镇公所内,将由乡勇押解入县,由县里处置,不出意外,将被处以死刑。
我是第二天早上离开镇公所的,回到店内,罗联镇内发生命案一事早已轰动全镇,一拨又一拨的人拥到保甲的店内来打听详情,店主人惊魂未定,一个劲往外赶他们,道:“都别乱嚼舌根,两位先生的事,镇里自然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死的是谁?没看清楚,只知道是个姑娘,我老汉活了一把年纪,可也没见过离了脖子的脑袋,当时只吓得腿软,哪里还敢去看是什么人的脑袋。你们想知道死了谁,一个镇上的,谁家姑娘死在了家里,还能不知道吗?”
围观的人群有人接声道:“还真是奇怪了,这一个晚上过去了,还就是不知道那阮货郎杀了谁家的姑娘。”
店主人道:“不可能!谁家死了姑娘难道家里人还发现不了吗?”
那人道:“就是这点奇怪,一夜过去了,阮货郎换青丝连姑娘脑袋也换走的事全镇都知道了,但就是没传出谁家死了人,你说这可不是奇怪么?”
旁边有人搭腔道:“许是那阮货郎从别的地方带来的,不是镇上的人,所以没人知道。”
店主人道:“不可能,我看那脑袋还血淋淋的,一路奔波,哪里能随身带着?这镇上都没传出什么人死了么?”
那人应道:“前几日倒是有个姑娘用青丝将自己吊死在了阁楼上,眼下正停尸在家呢,不过那姑娘是阮货郎来之前就自挂死了的,和那阮货郎可没什么关系。”
店主人“哦”了一声,这才发现我分开人群走了进来,连忙朝我道:“先生回来了。”
围观的人群见我回来,眼神之中多有畏惧,这些都是良善的山民,一辈子也不会和命案发生什么关联,见了和命案有关的人,即使知道不是我干的,却还是心中不安,仿佛我身上也带着杀气似的,店主人和我说着话,他们就纷纷找借口离开了,不一会儿,店里就只剩下我和店主人两个人。
店主人朝我感慨道:“怎么也料想不到那小阮先生是这般心狠的人,杀了人,还带了脑袋回来,险些吓掉我一条老命。”
我在桌旁椅子上坐下,道:“这也是让我不解的地方,假设那姑娘真是他杀的,他杀了人也就罢了,为什么还割了她的脑袋回来,且还故意拿给我看呢?”
店主人也疑惑道:“是啊,杀了人之后,不是正要掩人耳目吗,怎么他还故意给你看那脑袋?”
我托腮道:“这正是让人费解之处,再说他初来乍到罗联镇,何至于和人有什么深仇大恨,要杀人割头?”
店主人似乎脑袋不会转弯,只是应和着我,道:“是啊,何至于如此呢?”
我叹了一口气,道:“主人家,他昨天出去后可回来过么?”
店主人想了想,应道:“中午回来吃过饭后又出去了。”
我问道:“你可曾看见他回后屋去过?”
店主人断然道:“没有,吃完饭就出去,直接出去的,没回后面。”
我问他:“确定没回去过么?”
店主人道:“没有!我就坐在那和他说话,吃完中饭他就显得急匆匆的,直接就又推着车出去了。”
我“哦”了一声,心中暗想,如果阮郎那天回来过,将包裹放在了屋里,还有可能是被人偷进后屋,将那脑袋放入他包内的,可是他一整天没回过后屋,就是说那包裹他是一直随身带着的,那么那青丝是怎么变作一颗带发的脑袋而不被他发觉的?还是说他真的杀了那姑娘,割下脑袋藏在包里,然后又真的故意拿给我看,欲盖弥彰?所谓的被吓昏过去,只是他在装模作样?
我明明记得他那天晚上还喜滋滋地跟我说,那姑娘好像对他有点那个意思,他自己自然更有那个意思,可是转眼就去割了人家的脑袋,这实在让我接受不了。
我想着,忽然又记起了什么,问店主人:“据说现在还不知道死的什么人?”
店主人道:“是啊,真是奇怪,罗联镇就这么个小地方,谁家有人死于非命居然还没传出来,不知道怎么搞的,难道死的真的不是镇上的人?”
我还没回话,只见店主人又怯怯地道:“先生,店里出了人命,你可是还要住在这里么?”我以为他是担心我不愿再住在他店里,正要安慰他不用担心,一看他神情,这才明白过来,他根本不是怕我不住,而是怕我还要住在这里。
看来他也很其他的山民一样,将和人命有关的人都视为不祥之人,不想我再住在店里,但除了这里我又无处借宿,只得厚着脸皮央求他:“主人家,除了贵店,我实在无处可去,只得继续劳烦你,巡城马为人传书递信,干的也是功德事,你就容我打扰几天吧。”
店主人见我这么说,也觉不好意思,连忙答应下来。我回到后屋,见阮郎那张床空荡荡的,也有些黯然神伤,我们两张床相隔不过一尺多,恰好只容一人驻足。我坐在自己床上,想着昨晚离我不到二尺的距离,有一颗血淋淋的脑袋,又有点不寒而栗。
床头上那本书还在那里,巡城马往来奔波,又要替人捎带一些小物件,自然不能带太多自己的东西,我常年也只带一身换洗衣裳和一本消愁解闷的书。这书跟着我多年,早被我看得烂熟于胸,不过这两天却是一页也没翻。
我随手拿起它,那书在某一页处有折痕,我心想,我上一次是看到这里么?这书我看的次数实在太多,每一页都一样的熟悉,是以上一次我究竟看到了哪一页,记得并不清楚。
我将书装入包裹之内,本来罗联镇的家书都已经送达,要送出去的信也都已经收好,我早已可以离去,可是想起阮郎平时的说笑,活脱脱还是少年心性,怎么也不信他会去杀人。
在他身上净发生诡异事,我想,先是一路打听失散十几年的父亲,却在罗联镇上发现一个家大业大的女人后,固执地声称,她就是他的父亲,然后换青丝却换回一个脑袋。我叹了一口气,将包裹放好,决定再去一次镇公所。
到了镇公所门口,守门的乡勇听说我要见阮郎,顿时将头摇得像拨浪鼓,我央他:“我是巡城马,一路与他同来的,多少有一份情宜在,临行前来见见他,还请千万行个方便。”
那乡勇紧张地道:“罗联镇上从未出过杀人事件,这是要押解上县的人,镇长令我看守,责任重大,可不敢让你进去。”
我正要再央他几句,却见镇长闻声走了出来,见是我,一般人多少都会敬重传书递信的巡城马,他就道:“既是代写家书的巡城马,就让他见上一见也好。”那乡勇见镇长这般说,这才放我进去。
走进镇公所的小院,阮郎被关在一间屋里,此时正透过窗子看外面,见是我来了,顿时大叫:“先生,先生。”
门口的乡勇呵斥了他一声:“叫什么叫?”
他顿时就噤声不敢再叫。我看着镇长,镇长点点头,对门口站着的那乡勇道:“你到院门口去守着,让先生和他说上几句话。”
我感激地朝镇长点点头,镇长让乡勇去守院门之后,自己也就走入另一间屋内去,只剩我和阮郎隔窗相望。阮郎见人都走了,顿时朝我呜咽道:“先生,先生,我没杀人呐,呜呜,我怎么会去杀她啊。”
我皱眉道:“可是那脑袋怎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收青丝的包裹里?你告诉我,昨天你收了青丝之后,可曾回去过,将包裹放在屋内?”
阮郎摇头道:“没有,我回去吃了中饭后就又出去了,那包裹我一直随身带着,放在车上。”
他说得和店主人一样。我问他:“那你当时收的时候,确实只有青丝么?”
阮郎急了,叫道:“先生,你也不信我么?我如果当时收的是脑袋,在屋子里我会掏出来给你看吗?”
我凝视着他:“那我就不明白了,你一直随身带着的包裹,青丝怎么会忽然变成了脑袋了,如果说你昨日曾将包放了回去,倒有可能是有人将那东西偷偷放入你包内的,偏偏你昨日一整日都随身带着,既然这样,那包里的东西就只有你自己能放进去。”
阮郎看着我,想说什么,嘴角动了动,却又没发出声音来,我看他这幅模样,心中一动,立刻追问道:“你可是还有什么隐情没说,都到了这般时候了,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?再不说可就没机会再说了。”
他犹疑了一下,看了看四周,这才轻声道:“我知道人是谁杀的!”
我这一惊非同小可,阮郎居然知道人是谁杀的,马上高声追问道:“谁?是谁杀的?”
阮郎却又明显急了,朝我道:“先生,你轻声点。”
我只好耐住性子,压低了声音,又追问道:“是谁?”
阮郎看着我,轻轻道:“罗夫人。”
我瞠目结舌,没想到他居然会说出罗夫人来,阮郎见我不做声,又轻声道:“那天我收了青丝回来,又路经她家后院,她仍然叫我进去,我将车停在她家后院,跟她进去,她却又说,她丢了把剪子,我一看,那把刻着我名字的剪子果然不在那桌上。我思来想去,当时只有她有机会把那东西放入我的包裹。”
我有点生气,责问道:“这么重要的事,你怎么不说出来?”
他有点奇怪地看着我,轻声道:“我觉得她不会害我。”
我顿时哭笑不得,这时候他还在觉得那个女人是他爹,不会害他!我不去理他,打算去找镇长,无论如何要把他刚才说的事告诉镇长,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无辜地替别人送死。谁知我正打算去找镇长,镇长就从另一间房中探出头来,轻声叫我道:“先生,先生。”
我应声走了过去,镇长示意我进屋,又让我坐下,我正要跟他说有事相告,那镇长就搓着手,一直在屋内走来走去,像是有什么大事不能委决一般,我看得奇怪,正要开口,镇长就走到我身边,肃穆地道:“事情不好办了,先生。”
我奇道:“什么事不好办了?”
镇长抿了抿嘴,道:“先生一定觉得奇怪,货郎收青丝却掏出一个脑袋来,这么大的事,为什么一直不见有人报案,迄今也不知是谁家的姑娘遇害?”
我连忙点头,道:“大家也对此议论纷纷,莫非那姑娘真的不是镇上的人么?”
镇长严肃地看着我,摇了摇头,道:“在你和阮货郎来到罗联镇之前,镇尾的阁楼那里,有个姑娘用自己的一头长发,将自己吊死在阁楼上了,她无父无母,只身一人,这些天都停灵在家,镇里正准备过几日将她下葬。”
我听得有点不明所以,问道:“那又如何?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?”
镇长盯着我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道:“那货郎从包裹里掏出来的,正是那姑娘的脑袋!”
他话一出口,我马上寒彻骨髓,光天化日之下竟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颤。阮郎去收青丝,有一个姑娘将青丝卖给了他,结果那姑娘竟在他来之前就已经用青丝将自己吊死!
那死去的姑娘被一头青丝勒得慌,这才下楼将青丝卖给了换青丝的汉子。我不禁想起了在来罗联镇的路上,阮郎给我讲的那个故事——青丝结,或者青丝劫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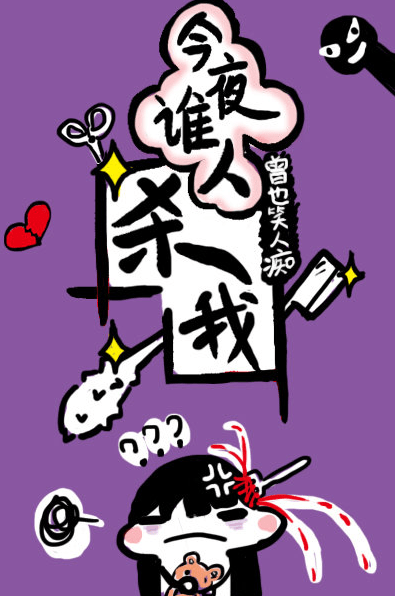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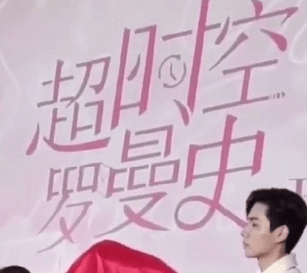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智能火网友
打卡!我是第一个!
智能火网友
写我?
智能火网友
突然聊到了一个话题 有些感慨 我们都没有判断任何人的资质。 我讨厌你不一定是你一无是处,只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会「恶意」解读。 我喜欢你不一定是你完美无瑕,只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会理解包容。 这世间哪来公平,每个人心理的天平都各不相同,世人都有偏爱,何必庸人自扰追求绝对公平。
智能火网友
加油~是我喜欢的文风~
智能火网友
支持你鸭,小姐妹 阿笙留
智能火网友
很好看,不错不错,继续更新吧,我会永远支持你
智能火网友
【系统提示】日常任务:调戏作者大大!
智能火网友
为七打call! 原谅我这么几句! 很爱七写的文,笔芯呐♡
智能火网友
爱死你的溶图
智能火网友
感谢收藏、关注及鲜花,这些都是作者的动力,希望大家拿鲜花?“砸死”我,谢谢!????????????????????